1、武林外传谜题之一
时代的喜剧与喜剧的时代
2、武林外传场景解密
——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喜剧创作的特点
3、武林外传位置
万芳
4、给我找到武林外传
内容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喜剧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的到来、话剧生产机制的更迭改变了人们对喜剧的认识和整个话剧生态,并由此带来了新世纪喜剧内涵与意蕴的变化。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中国大陆喜剧的“商业化”“发现身体”“即兴”“敞开”四个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喜剧自身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发展,还展现出时代文化心态的幽微之处。
关键词:21世纪 喜剧 商业文化 大众文化5、武林外传武林秘辛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6、武林外传网游任务攻略
文章编号:0257-943X(2021)03-0030-11
7、武林外传路线
万芳,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喜剧、华文文学、网络文学、女性文化。代表作有《历史的暧昧叙事:中国新历史小说中的声音》(Dubious Narrative of History: Voices in Chinese New History Novel),刊于《汉学研究》(Confuci Acadèmic Journal);《新上海怀旧叙事:<繁花>中的老建筑》 (New Shanghai Nostalgia: Old Buildings in Blossoms),刊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写作的异乡人:以张翎为代表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姿态》,刊于《当代作家评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重写文学史”思潮为中心》,刊于《华文文学》;《浅议新世纪以来的喜剧创作》,刊于《戏剧文学》。另有小说刊登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
8、武林外传武林密探
一、时代的喜剧
9、武林外传神秘地点269.37
(一)新世纪社会背景的变化
10、17173武林外传
展开全文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此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如果说1990年代中国内地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那么对2001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而言,市场经济下的消费逻辑真正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笼罩性背景。市场成为21世纪话剧必须面对的考验,如何吸引更多观众,如何获得较高的票房,逐渐成为话剧人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在21世纪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就是网络的发展和普及。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第42期)》,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共有超过8亿的网络用户。[1]网络的急速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相互交流和日常娱乐的方式,并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文化。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话剧、小说、电影、音乐等文化类型与网络文化相互纠缠、相互渗透,发展出很多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而喜剧由于其内在的娱乐属性,与网络文化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与此同时,话剧的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家降低民营团体进行商业性话剧演出的门槛,民间资本、艺术学校、海外机构都加入到戏剧的制作中,与国营剧团展开竞争。投资相对较低、容易获得观众青睐的喜剧成为各类戏剧制作团体的首选,21世纪的剧坛几乎成为喜剧的天下。目前的喜剧生产聚集了多方力量,既有像“开心麻花”“戏逍堂”这样的商业公司,也有“孟京辉戏剧工作室”这样的个人工作室,还有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样的国有剧团,它们共同促进了21世纪喜剧的繁荣。
(二)喜剧内涵与意蕴的变化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对喜剧进行如下描述:“喜剧的目的是和人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目的一致的,这就是使人从激情中解放出来,对自己的周围和自己的存在永远进行明晰和冷静的观察,到处都比发现命运更多地发现偶然事件,比起对邪恶发怒或者为邪恶哭泣更多地嘲笑荒谬。”[2]从本质上说,喜剧是生命力的直观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也是人们对自我、外界、人生的一种理性观照与超越。同时,喜剧又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它会随着所处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1.喜剧的泛化
进入21世纪后,喜剧的概念产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喜剧的泛化。传统的喜剧框架在新世纪的剧坛上逐渐淡化,越来越少的创作者会用“幽默喜剧”“抒情喜剧”“讽刺喜剧”这样的概念来定义自己的创作,这些不再成为对喜剧类型的界定,而成为喜剧中的不同元素。无论是滑稽、幽默,还是辛辣、荒诞,都是为了“笑”而服务。它们在同一部剧中共存,共同组合成带有复杂况味的喜剧。“笑”成为喜剧的唯一定义,无论是喜悦之笑、辛辣之笑、自嘲之笑、苦涩之笑,全部糅合在一起,成为喜剧的统一标签。这种敞开与跨越使得喜剧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更新了人们对喜剧原有的想象和期待。
喜剧的泛化更体现在喜剧外延的扩大上。西方理论界从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开始就对“什么是喜剧”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我国虽然是从王国维引进“喜剧”概念开始才有了相关的理论体系,但喜剧传统同西方一样悠久。[3]进入21世纪之后,原有的喜剧概念遭到了冲击,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成为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它们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消失,转而更多地进行相互渗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题材都可以做成喜剧,任何体裁都可以变身为喜剧,喜剧的范畴被大大地拓宽了。这种变化一方面扩展并加深了人们对喜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定义喜剧、研究喜剧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所讨论的21世纪以来的喜剧,以“笑”为核心,无论是欢快的笑、自嘲的笑、轻浮的笑还是辛辣的笑,全部都糅合在一起,成为定义21世纪喜剧的结构性元素。具体来说,笔者将21世纪以来的喜剧区分为大众文化主导的喜剧和精英文化主导的喜剧。其中,大众文化主导的喜剧包括爆笑喜剧(如《想吃麻花现给你拧》《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和造梦喜剧(如《硬如人心软如你》《钱多多嫁人记》),精英文化主导的喜剧则包括针对社会问题的喜剧(如《蝴蝶变形记》)和荒诞化的喜剧(如《我爱桃花》《秀才与刽子手》)。[4]
《我爱桃花》演出剧照

2.喜剧精神的变化
在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大陆话剧所体现出的喜剧精神总是离不开社会性,一直强调一种“有意义”的笑。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逐步被强调,但那时的喜剧精神仍然是有着强烈的启蒙立场的,喜剧自身的娱乐性并没有得到凸显。直到1990年代,喜剧的娱乐性才逐步得到彰显。而喜剧中“游戏精神”的真正实现,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弗里德里希·席勒等人都曾经对“游戏”进行过论述。在他们那里,“‘游戏’是与‘自由活动’同义而与‘强迫’对立的”,与“游戏精神”相背离的是主体的非自由状态。[5]对于一个自由的个体来说,游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6]这种游戏性,在21世纪之前的中国大陆喜剧中是非常罕见的,只有进入21世纪以后,喜剧里才大量出现游戏元素。“游戏论”是对此前一直笼罩着喜剧的“工具论”的解构,喜剧一直受到忽视的“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转而重视观众的需求。
娱乐功能的强化让狂欢化成为21世纪以来喜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狂欢化(carnivalization)是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的小说和中世纪的一些笑文化之后提出的理论,它与狂欢节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娱乐色彩和平民本位性:“从本质上来看,笑具有深刻的非官方性质;笑与任何现实中的官方严肃性相对立。”[7]不过,巴赫金的狂欢化并不是对娱乐至死的追求,其内核是笑的自由精神。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爆笑喜剧和造梦喜剧成为喜剧的主流,狂欢逐渐成为吸引观众的一种商业策略。这一策略极大地彰显了21世纪以来喜剧的平民本位性,话剧创作者不再试图教育或者启蒙观众,而是成为了观众声音的倾听者,观众的审美倾向与趣味成为喜剧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传统狂欢化的内核在这些喜剧创作中也渐渐褪色,无论是对正统观念的疏离,还是人与人之间无拘无束的交往,都不再是某种精神的体现,而是对观众喜好的迎合。可以说,21世纪喜剧精神中的狂欢化,正在远离巴赫金式的狂欢,转而建构起富有时代特点的全新内核。
二、总体特征
(一)“商业化”
商业化既是21世纪以来喜剧的重要特征,也是这些作品创作的大背景,更是影响21世纪以来喜剧创作并塑造其特征的关键因素。由政府部门支持的戏剧剧团是戏剧主要的生产单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到了1990年代后期,在这个生产体制之外集结了很多新的力量,戏剧制作体制越来越多元化。例如,“火狐狸剧社”最先开始了个人投资方式,《驿站桃花》则是较早由公司投入的戏剧作品。2005 年,国家文化部等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简称《意见》),降低了民营团体进行商业性话剧演出的市场准入门槛。《意见》出台后,民间资本、海外资本、艺术学校等各类资源都介入戏剧的制作之中。这些民间力量活跃了戏剧生产,由于营利需要,他们将目光投向容易获得观众青睐的喜剧创作,占领了话剧市场的大量份额,国有剧团因此受到冲击。为了应对民间戏剧强有力的竞争,国有剧团也开始大量创作喜剧,喜剧占领了21世纪话剧领域的绝大部分市场。可以说,喜剧创作在21世纪的蓬勃发展,是与商业化大潮紧密关联的。
具体来说,21世纪以来喜剧的商业化首先体现在喜剧的品牌化上。“戏逍堂”“开心麻花”“雷剧场”等都是著名的喜剧品牌,这些品牌并不把喜剧视为一种艺术,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商品。这些喜剧创作团队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进行喜剧创作,在尽力使喜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标准化的同时,也积极根据核心观众的偏好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其创作的喜剧不是艺术上的创新,而是内核以及模式上的重复,以此为团队旗下的喜剧贴上固定标签,从而巩固该喜剧品牌在观众心中的形象,确保核心观众群的稳定。在此模式之下,从生产到推广,整个喜剧的链条都被彻底商业化了。
除了将喜剧生产链条进行模式化处理以打造清晰的品牌形象,这些喜剧品牌还提出了诸如“贺岁喜剧”“减压喜剧”等概念。2001年底上演的《翠花,上酸菜》在票房上大获成功之后,话剧界掀起了一股创作贺岁喜剧的热潮。导演田有良在2003年底和2005年初又先后推出了《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和《淡了,加点韭菜花》两部贺岁喜剧,刘艳则趁着“翠花”系列的热度,推出了《翠花,上酸菜》(2003版)、《翠花快乐六人行》等贺岁喜剧。[8]这类喜剧的“笑”的目的非常单一而明确,并不是为了承载什么复杂的内容,而是让观众减压,让观众通过笑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排除出去。这类喜剧自觉地充当了现代人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工具。《糊涂戏班》制作人李胜英就明确表示:“又快过年了,在经历了一年的紧张和压力后,能来剧院看一出爆笑喜剧,无疑也是一种释放和宣泄。”[9]贺岁喜剧对娱乐性的推崇很快演变为对爆笑和减压的追求,“开心麻花”“戏逍堂”“雷剧场”等剧团制作的很多喜剧从“贺岁”出发,渐渐演变为全年性的对爆笑的追求,“过年时全家乐一乐”变成了“日常的笑一笑减压”。2007年12月,雷子乐笑工厂成立,推出了“原创减压喜剧”的理念,直白地喊出了“减压戏剧,就是让你笑”的口号。[10]这些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增强了喜剧的娱乐性,在21世纪娱乐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走入剧场。[11]
《糊涂戏班》演出剧照
除了依靠票房,广告植入也是重要的盈利手段。在中国大陆的喜剧中,“麻花”系列剧是较早在剧作中尝试广告植入的。在高峰的时候,一台喜剧中会出现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广告植入。不仅是品牌化的喜剧创作团队会进行广告植入,知名话剧导演们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在田沁鑫的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出现了牛奶和衣服的广告植入。舞台上摆放着印有牛奶品牌名称的冰箱,台词中也加入了该品牌的广告词。此外,演员们还在舞台上穿着赞助商提供的衣服。孟京辉导演的《盗版浮士德》中也出现了服装品牌的植入,话剧舞台立体、丰富的表现为服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展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话剧获得商业赞助实现了赞助商与话剧制作团队的双赢。一方面,提供赞助的品牌收获了不断上涨的销售额[12],另一方面,话剧有了更加充足的预算,可以在不影响话剧质量的前提下降低票价,以推动更多的观众走入剧场。2010年,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在谈到话剧广告赞助时表示:“话剧需要在企业强有力的支持下推广,国话的作品一直在为低票价高质量而努力,这样的商家赞助,其实也是支持百姓走进剧场。”[13]然而,话剧的广告植入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话剧制作方无法平衡艺术性与商业性,就会出现广告植入过于刻意的情况,这极大地影响了话剧质量。例如,田沁鑫在《夜店》中所进行的广告植入就因为过于露骨而引起了巨大争议,导致其不得不在后几轮的演出中将植入的广告删除。
随着中国大陆地区消费文化的不断成熟,近年来,很多喜剧在商业化方面进行了更加多元的尝试。例如,话剧《神马都是水浒》与联想集团进行深度合作,不光在话剧中进行了广告植入,还将剧中形象提供给联想集团,作为联想集团旗下新款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的图标。这种将人物形象商标化的方式,更加彻底地开发了喜剧中的商业化资源。
(二)“发现身体”
1.肢体动作的大量加入
纵观21世纪以来的喜剧,大量肢体动作的加入成为一个异常鲜明的特点。例如,在《蝴蝶变形记》中,演员们的动作狂躁、扭曲、张扬,他们经常在泥沙中打滚;而《满城全是金字塔》中,则充满了夸张的动作和扭动的舞蹈。大量的肢体动作为21世纪以来的喜剧带来了一种狂欢的民间气息。
这些肢体动作的出现是有着深厚的中西方文化资源的。一方面,这是西方戏剧中民间传统的进入。西方知识界重理性认知的文化传统造就了语言在戏剧中的中心地位,戏剧语言的发达使知识阶层作为启蒙者的地位与趣味得以充分彰显。相比之下,形体表演则因为更容易被大众理解而缺少了几分神圣感,在文学化的戏剧传统中,这样的表演风格受到了压制。这不仅是因为它暴露了纵欲狂欢的民间习性,更重要的是,它隐藏着挣脱知识阶层控制、实现完全民间自主的企图。[14]西方社会到了20世纪,随着理性危机的爆发和对现有文化体制的反抗,其戏剧传统发生逆转,由以语言为中心的“剧本化”转成以表演为中心的“剧场化”。20世纪60年代,位于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出现的大量以形体表演为中心的先锋派戏剧,就是这种戏剧传统发生逆转的鲜明体现。[15]
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古典戏曲传统的“现代唤醒”。与西方戏剧的“文学性传统”相对应,中国戏剧的传统则可被称为“人体性传统”,即在口头语言系统之外,建立了独立的、甚至拥有更高地位的形体语言系统。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动作除了配合人物的台词,更是具有补充和强化剧情的功能。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曾说:“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和西洋演剧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在舞台艺术的整体中,我们把表演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16]这种“人体性传统”与中国的传统仪式有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仪式中礼仪规范的同构,体现着精英主义的教化立场。[17]而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戏曲中还有许多完全独立于台词和剧情之外的动作,如翻跟头之类的杂耍武艺,承担的是吸引观众的剧场功能,体现了对平民大众娱乐需求的重视,与西方戏剧传统的精英立场相比,有着鲜明的平民化姿态。
2.“赤裸”的深层含义
除了肢体动作之外,21世纪以来的喜剧还出现了大量赤裸的情节。《天上人间》《在床上》《乌龙山伯爵》等喜剧中,都出现了赤身裸体仅穿着遮羞衣物的人物,其赤裸本身就为戏剧带来了笑料。“赤裸”在《蝴蝶变形记》中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全剧的尾声部分,小城的居民们用铁锹铲土,活埋了所谓的罪人黑豹,又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男人们全都光着上身,而女人们也仅身着内衣。孟京辉对这样的情节设置给出了自己的诠释:“这是要呈现人蜕皮重生,全部脱掉后,再换上一身特干净的衣服,重新光鲜做人。”[18]
孟京辉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赤裸本身所隐含的“本来面目的人”(unaccommodated man)的深层含义。在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的现代转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象征,即衣服成了陈旧的、虚幻的生活方式,而赤裸被用来象征新发现的和新体验到的真相。在这种象征下,脱衣服成为了一种解放精神和走向真实的行为。这种含义早在现代时期开端的莎剧《李尔王》(King Lear)中就出现了。在《李尔王》的第三幕第四场,李尔王遇到了化装成乞丐、一丝不挂的爱德加。看到他,李尔王发出了感叹:“你才是原本的东西:本来面目的人……”在这样的气氛中,李尔王脱掉了自己的王袍。李尔王相信,脱衣服的行为把自己降到了一种最低程度的生存状况,但这却是走向一个完整的、本来面目的人的第一步,因为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与另一个人的联系。[19]也就是说,在李尔王这里,他借脱衣服这个行为,第一次真正成为了“本来面目的人”,走向了精神解放与不加掩饰的真实。这种通过脱衣服而带来的成为“本来面目的人”的张力,在2019年版的《天堂隔壁是疯人院》里得到了直观的展现。在这个版本中,饰演吴所的何易加入了一个2001年版和2010年版里都没有的动作:脱掉上衣。孤独的、失意的、渴望交流与被爱而不得的吴所,经由这个动作,情感喷薄而出,撕开了所有加诸自己身上的荒诞的外衣,挣脱胆怯与迷惘的束缚。由此,2019年版里的吴所,有了区别于前两版的鲜明气质,更加贴近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年轻观众的内心世界,直指这个时代微妙的精神内核。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天堂隔壁是疯人院》(2019)
3.“发现身体”的两重性
在现代艺术中,身体被赋予了各种意义,它们与巴赫金所定义的拉伯雷小说中的身体具有同等意义,代表着对固有束缚的反抗,扎根于民间幽默中。[20]21世纪以来的大陆喜剧中所出现的身体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身体在这里充满了民间性,它成为民间文化的载体,代表整个民间社会对精英文化发起挑战。因此,当身体刚刚出现在喜剧中时,是具有先锋意义的,是具有解放意味和平等色彩的。
然而,在这个被商业文化笼罩的现代社会,身体逃脱不了被消费的命运,其所具有的解放意味很快就消散在前赴后继的对这一元素的消费中。身体不再是精神解放的象征,反而成为一种对欲望消费的刺激与暗示。正如南帆在《身体的叙事》中所言:“的确,身体隐含了革命的能量,但是,欲望以及快感仍然可能被插入消费主义的槽模。身体虽然是解放的初点,可是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21]
(三)“即兴”
21世纪以来,喜剧的即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很多喜剧在排练中先按大纲即兴表演,然后再根据演员的表演形成剧本。“开心麻花”、“戏逍堂”、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等剧团的喜剧都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排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在正式演出时抛开剧本,根据观众的反应即兴发挥。例如,在《Q大道》的演出过程中,由于观众的情绪不高,演员临时加上了派送糖果的部分;而《硬如人心软如你》为了追求火爆的剧场效应,也曾随机根据观众反应在演出中插入礼品派送环节。所有这些都成为喜剧演出的一部分,从而让每一场演出都变得不可还原、不可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喜剧不再只是一个固态的名词,而成为了永远在变化的动词,是一个由演员、导演、表演、剧场、身体动作等要素结合而成的永远处于流动中的活动。
“即兴”这个特点体现了21世纪喜剧创作中剧本的弱化。换言之,在这个阶段的喜剧中,剧本已经退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演员的表演逐步成为一个剧的核心,甚至其内容都根据演员的表演而进行确定。于坚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观察到了这种变化,这个在当时属于先锋话剧的特点,在21世纪的喜剧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戏剧的传统方向被改变了。它是导演和演员在现场的活动,在这种充满繁殖力的活动中,导演被创造出来,演员被创造出来,剧场被创造出来,台词被创造出来……剧本在最后出现,成为戏剧的历史的记录,而且它永远没有定本。戏剧不再是剧本的奴隶,它的文本就是它自身的运动。”[22]
同时,“即兴”在21世纪喜剧中的大量出现也体现了喜剧的商品化,换言之,观众开始被当作消费者加以对待,而不再是需要启蒙的对象。由于观众是喜剧这一商品的消费者,所以观众的任何反应都被出品方加以郑重对待。如果剧情吸引不了观众,就加入互动,甚至派送礼物,一切都不以喜剧本身的完整性为重,而是围绕着观众的感受进行。更重要的是,这种即兴是一种当代社会的投射。由于喜剧具有极强大的结合能力,能够快速整合各种信息,展现一个迅速变化、喧哗不已的世界,因此能够从多个方面模拟当代社会。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喜剧所体现出的“即兴”既是对戏剧生产本身特质的一种展示,更是对“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流动性的复制和塑形。
(四)“敞开”
21世纪以来的喜剧深受各种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其中一个突出方面是艺术观念的影响。例如,行为艺术这种观念艺术,就非常重视在特定环境中所构成的特定意义,非常强调互动性和即时性,这些都对这一阶段的喜剧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来说,对21世纪以来的喜剧产生较大影响的艺术种类和表现形式主要有:行为艺术、东北二人转、以冯小刚市井电影为代表的“京味调侃”、以赵本山作品为代表的东北小品、网络文学和网络流行语、多媒体艺术、传统相声、海派滑稽戏等,不同艺术元素的融入让这个阶段喜剧的意蕴变得更加丰富。例如,《市井三国》大量使用了快板、评书、评弹、戏曲等艺术形式;《俗世奇人》加入了“梅花大鼓”“天津快板”“京韵大鼓”等曲艺和锣鼓家什、古玩等民间艺术,并且把芭蕾舞《天鹅湖》也加入其中,强烈的对比使得该剧充满了幽默、诙谐的色彩。
在多类型的文化中,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学对这一阶段的喜剧产生了格外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大量网络小说改编为喜剧,如根据博客名人介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裸婚》、根据网络作家三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和空姐同居的日子》。进入21世纪后,话剧观众的年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话剧主体观众的年龄在40岁左右,而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体观众的年龄则降到了35岁以下。[23]由于网络小说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故而将它们改编成话剧一方面迎合了话剧主体观众的趣味,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些网络小说的人气,吸引大量的原著的粉丝走入剧场。这类改编除了体现21世纪喜剧的商业逻辑之外,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大批喜剧的创作。网络文学由于门槛较低,所以每日都会有大批小说发表在各类文学网站上。为了获得更高的点击量,一个极具噱头的名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创作习惯不仅影响了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喜剧,也影响了那些并非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喜剧创作。《和空姐同居的日子》《在床上》《艳遇十小时》这类剧名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而《裸婚》《嫁给经济适用男》等剧名则紧跟当下最引人关注、最具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除了剧名,网络文化强烈的娱乐色彩也对21世纪的喜剧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新世纪后,爆笑喜剧和造梦喜剧在数量上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以《借我一个维塔斯》《满城全是金字塔》为代表的爆笑喜剧并不追求深刻性,既不讽刺那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也不对人生与自我进行思考,更没有实现理性超越,其唯一的追求就是让观众笑,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相比于爆笑喜剧,《21克拉》《与奋斗有关的日子》等造梦喜剧不仅让观众笑,还试图为观众提供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能带来短暂慰藉的梦境。这两类喜剧的创作深受网络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两类喜剧正是网络时代的产物。爆笑喜剧在台词中融入了大量的网络用语。网络小说中制造爆笑场景的一项常用手法就是将网络用语进行包装,融入人物对话或剧情中,从而达到喜剧效果,这一手法在网络文学创作里被称为“融梗”。21世纪的爆笑喜剧在创作中也大量采用这种“融梗”手法。例如,《史上第一混乱》中就融入了网络流行语,在制造笑料的同时,也大大拉近了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网络文学作为兴起于21世纪的流行文化,深受日本动漫作品及相关文化的影响。随着日本“轻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网络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广受欢迎的以“纯爱”为标签的言情小说。[24]这类作品并不着力营造浪漫的氛围和浓烈的感情,而是变得节奏轻快、语言幽默。网络时代的审美讲求“轻”,复杂的剧情、激昂的感情以及过于缠绵的氛围都由于过于沉重而成为被舍弃的创作要素。这种审美倾向对“着力为观众虚拟一个完美世界”的造梦喜剧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这类喜剧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武林外传》为例,这是何念和宁财神共同打造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是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的前传。这部剧讲述了电视剧中始终未出场的莫小宝在真挚的爱情与唾手可得的财富之间几经摇摆,最终选择了真爱的故事。虽然这部剧围绕着莫小宝的感情线,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但并没有大力渲染缠绵悱恻的浪漫氛围,也没有着力刻画人物之间的深情,而是把对爱情、浪漫、理想生活的追求都包裹在密集的笑点、轻松的剧情,以及在搞笑与正经间收放自如的角色里,解构了古典主义的浪漫与激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充满梦幻而又轻松愉快的完美世界。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武林外传》演出剧照
三、喜剧的时代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指出:“今天的世界变得肢体不全,喧嚣不已。”[25]这意味着,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悲剧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进入了碎片化的喜剧时代。在国内,董健也在《迈入21世纪的中国戏剧》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新一代人的世界观里,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心目中”,“喜剧(与平民本位有关,与充满批判与超越精神的幽默感相联系)的精神将会大大高扬”。[26]无论学者们抱着怎样的态度,在喜剧时代已经来临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代,喜剧越来越成为时代文化的典型表达方式。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商业化、发现身体、“即兴”和“敞开”,这些21世纪以来喜剧创作的特点,展示出这个时代文化心态的幽微之处。
讨论喜剧与大众文化,或者说在大众文化的框架下看待喜剧,有着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是在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在我国消费文化形成的初期,市场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先锋的力量,对于当时看起来强大的、僵硬的戏剧体制来说,市场成为最有力的抗衡空间。也就是说,在当时,商业化有助于戏剧艺术复归人性,有助于个人欲望和个人价值获得应有的尊重。
然而,在消费文化全面进入喜剧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格外复杂起来。一方面,受到消费文化泛滥的影响,喜剧正在变成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所认为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它再次成为一种控制民众的手段,只不过这次控制民众的力量变成了资本。[27]这种文化向民众灌输醉生梦死的娱乐,让民众失去反思社会以及自身的能力,从而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28]而在另一个方面,如果从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葛兰西转向”(the Gramscian turn)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则会发现喜剧正在成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官方文化的角力场。[29]事实上,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只能被动接受,他们通过文化消费行为,反向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必须要考虑民众的趣味,否则他们的文化商品就会落入无人消费的境地,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方式,参与了这场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从这个角度来说,喜剧作为一种平民本位的文化,正是民众争夺文化话语权的绝好阵地,很多为喜剧时代摇旗呐喊的人所看重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彰显的平民性。
然而,这种民众通过消费来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具有真正的平民性,因为绝大多数真正底层的人们是没有能力支付观看喜剧的费用的。张柠在《小剧场与都市文化消费》中对都市的文化消费进行了分类:“大都市的文化消费类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电视和全国性报纸等主流媒体为核心的公众消费;一种是以畅销书、杂志、专业小报等边缘媒体为核心的阶层消费(按年龄、性别、爱好划分);还有一种是以音乐厅、展览馆、小剧场等都市文化为核心的阶级消费。一般来说,第三种文化消费群体中,基本上没有打工族和赤贫的流浪者,而主要是白领、知识分子、艺术精英、文化官员。”[30]这种所谓的“平民性”的危险之处正在这里,它给了人们一种“平民性”的印象,反而遮蔽了真正身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大多数。这可能是研究者们从大众文化视角来审视21世纪以来喜剧时需要格外加以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第42期)》,2018年8月。
[2]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著,张玉能译:《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
[3] 参见张健:《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2—85页。
[4] 关于21世纪以来这两类喜剧类型的详细分析,见笔者另一篇文章《浅议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喜剧》,《戏剧文学》,2016年第11期。
[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48页。
[6]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著,冯至、范大灿译:《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7] 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élène Iswolsk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66-67.
[8] 万姗姗、张健:《浅议新世纪以来的贺岁话剧》,《戏剧文学》,2006年第5期。
[9] 丁盛:《让你笑个够——英国闹剧〈糊涂戏班〉下月登陆上海》,《话剧》,2004年第4期。
[10] 王庐璐:《浅谈当代“减压戏剧”》,《中国戏剧》, 2010年第5期。
[11] 吴丹:《以“减压”为名的话剧》,《北京青年报》,2009年2月27日。
[12] 满岩:《先市场后艺术:话剧〈盗版浮士德〉年初清算》,《北京晚报》,2000年1月23日。
[13] 和璐璐:《〈红白玫瑰〉也要广告植入》,《北京晨报》,2010年3月22日。
[14] Marvin Carlson, Theories of the Theatre: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urve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Present. Expanded ed.(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28.
[15] Sally Banes, Greenwich Village 1963: Avant-garde Performance and the Effervescent Bod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0.
[16] 程砚秋:《程砚秋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48页。
[17]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18] 《孟京辉〈蝴蝶变形记〉亮相蜂巢剧场》,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news.cntv.cn), 2011年3月28日。
[19]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0), 105-110.
[20] 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303-310.
[21] 南帆:《身体的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第81页。
[22] 于坚:《棕皮手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02页。
[23] 卢珊:《2005年以来中国商业话剧泛喜剧化现象研究》,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
[24] 日本“轻小说”与日本动漫作品有着深厚的联系。大量轻小说由动漫作品改编而来,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轻小说被改编成动漫作品,或配有漫画风格的插图。轻小说跳跃的节奏,大量的对话、短句,以及拟声拟态词的语言风格,都深受动漫创作的影响。

[25] (瑞士)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著,叶廷芳译:《迪伦马特喜剧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26] 董健:《迈入21世纪的中国戏剧》,《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
[27]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7), 120-167.
[2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1.
[29]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no. 2 (1980):57-72.
[30] 张柠:《小剧场与都市文化消费》,《南方周末》,2002年2月8日。
(作者单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
扫码关注我们
《戏剧艺术》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扫描小程序二维码
在线阅读
《戏剧艺术》电子版
关于我们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创刊于197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以繁荣戏剧研究,推进戏剧教育事业为己任,坚持古今中外兼容、场上案头并重,关注戏剧热点问题、鼓励理论创新,力推新人新作,曾以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为学界所瞩目,又以系统译介国外当代戏剧思潮、及时发表戏剧学最新优质研究成果为学林所推重,是国内最重要的戏剧学学术期刊之一,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投稿须知
《戏剧艺术》是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学报,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本刊奉行“ 理论与实践互动、传统与现代交辉”的学术理念,设有“戏剧理论与批评”“古典戏曲研究”“现代戏曲研究”“中国话剧研究”“表导演艺术研究”“舞台美术研究”“戏剧教育研究”“跨文化戏剧研究”“国外戏剧思潮”“国别戏剧研究”“学术动态”等栏目。为进一步提高本刊质量,欢迎广大作者惠赐 富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的佳作,尤其期盼 关注当前戏剧实践、学理性强的力作。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力求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现象,务请作者文责自负。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及教育部有关通知,希望作者来稿时标明和做到以下几点:
1.作者简介:姓名及二级工作单位(如,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
2.基金项目:含来源、名称及批准号或项目编号。
3.内容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篇幅为200-300字。
4.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5.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格式如下 (参考2019年以来我刊):
(1)注号:用“①、②、③······”。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请注意各注项后的标点符号不要用错):
A.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外文版著者、期刊、论文集、报纸等采用芝加哥格式: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姓在前、名在后,之间用逗号隔开,首字母大写。书名、刊名用斜体。
F.译文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并用括号括起。
本刊鼓励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平易晓畅、言简意赅的文风,希望稿件以1万字左右为宜。论述重大学术问题的论文篇幅可不受此限。本刊投稿邮箱: [email protected];暂不采用其他公共投稿系统。务请标明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联系电话。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录用或修改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文章一经采用,将通知作者提供定稿电子版以及 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建行或交行优先)支行、银行卡号码、手机号等信息,以便发放稿酬。
特别声明:本刊从未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若发现类似信息,可视为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举报。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站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相关机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 制作:史晶
• 责编:吴靖青
• 编审:李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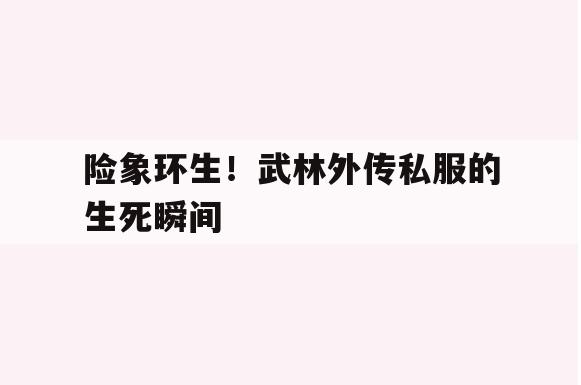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